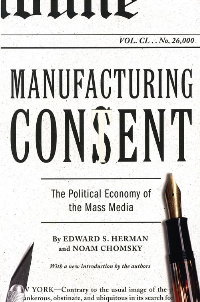有幾位站在人類知識生產分工機制的金字塔上層(來自Yale、Harvard、MIT等機構的博士訓練),而有志於成為專業學者的朋友,與我質疑辯難:關於自我教育者對知識的看法,以及學習的策略問題。
關於學習策略的質疑,包括:專業學者的社會地位有利於學習(便於取得高級知識),專業學者未必是受限於領域的人(列舉「大儒」或「通人」的例子),等等。
這些問題都很容易獲得共識。第一,專業學者取得高級知識比常人容易太多(時間、資源、近用權),因此要成為追求常識的人,如果有本事先成為專業學者,當然也不錯。但是當代學術分工過於精密,競爭又激烈,資淺的專業學者通常必須花費大量時間在出版,而出版講究的是在特定領域有新的貢獻。換句經濟學的話說,專業學者必須開發、剝削自己的比較優勢(comparative advantage)以避免在競爭中遭到淘汰。而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,結果就是職能的分化(differentiation),專業知識因而遠離了常識。因此作為一個專業學者,對於常識的追求,利弊難以衡量,通常取決於個人的能力和決心。
這就聯繫到第二個問題,有多少專業學者能夠成為通人、大儒?在這個問題上,每位有志於成為專業學者的朋友都同意:很難、很少。我想要補充一點,當代的(我們所認為的)通人、大儒,其知識領域看起來似乎比過去的通人、大儒來得狹窄。舉個例子,發展社會學家Peter Berger,政治學家Samuel Huntington,從現在的標準來看,好像很了不起了,年紀大了,是大師了。但你看看他們的著作的深度、廣度,比起Max Weber又如何呢?而Weber並不是專業學者。當代專業學者要成為大儒,太難了。而自我教育者根本不打算成為大儒,因為他做不到。
除了學習的策略之外,最主要的爭點,就是:專精一門知識,是不是旁通其他知識的必要途徑?或至少是比較有效的途徑?
對於專業學者而言,這是非常強有力的論據。他們認為,知識到了一個層次,都可以觸類旁通;因此應該要專攻一門知識,到了一個程度再推而廣之。
我的問題是:那麼,到了什麼層次,知識可以觸類旁通?到了什麼程度,可以學習其他的知識?正在讀博士的人會說,博士讀完才夠。副教授會說,等到成為被肯定的學者才夠(或得到終身教職才夠)。那麼為什麼不是大學畢業生就擁有足夠的專業知識,足以追求更廣的常識?專業學者有一個傾向,會過度強調專業學術訓練的重要性,以及從學術生產的規格,來判斷知識的價值。但事實上,學術生產的規格,究竟是把他們帶向觸類旁通,還是以井觀天?或是真實的生活體驗、觀察、甚至文學閱讀,更能使人觸類旁通?
另一個問題是,專業學者多傾向用自己的理論和語言,去解釋一切現象,如果這就是所謂觸類旁通的話。於是自然科學要主宰社會,經濟學要殖民人類感情。透過把一個學科的理論凌駕於所有現象,這些專業學者是真的更瞭解其他人、其他事情嗎?而透過許多年的專業學者辯論、整合、突破,最後,他們會「發現」許多其他人早就知道的常識。比如說,新制度經濟學派(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),「發現」了市場不是唯一的經濟機制,「發現」了政治與法律制度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。從Coase在1937年發表廠商理論,到1991年他獲得諾貝爾獎,1993年North也獲得諾貝爾獎,他們「發現」了過去經濟學家不知道(或因為經濟學的專業理論訓練而不願相信),但任何一個政治學生都知道的事情。
我一點都不會意外,如果公元2050年,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某個華人經濟學家,表揚他用數學公式證明孔子和佛陀的理論,是增加人類的整體功利(Utility)。但我不想等到那時候,再從經濟學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思想與佛學。
因為自我教育者可以「現在」就去讀論語、讀佛經。不需要什麼專業訓練。
從專業學者的標準來說,知識是要發表在期刊上才算擁有。但對於自我教育者、一個追求常識的人,知識卻是讀懂了、聽到了、想通了,就是擁有。因此對於專業學者,要成為通人、大儒,必須將知識在出版的著作裡整合。而對於追求常識的人,他要將知識在人的行為與生活中整合。
當然,一個專業學者,還是有可能是一個擁有常識的人,因為他也可能在人的層次,整合、實踐他的各種知識。專業學者與自我教育並不衝突,重點是在,有沒有對知識的真誠、以及足夠的好奇心。
是要在人的層次,成為擁有常識的人;還是要在知識的層次,成為博學的人?這是自我教育者必須自我追問的問題。
圖:Yale University圖書館,攝於去年夏天